回应刺激的能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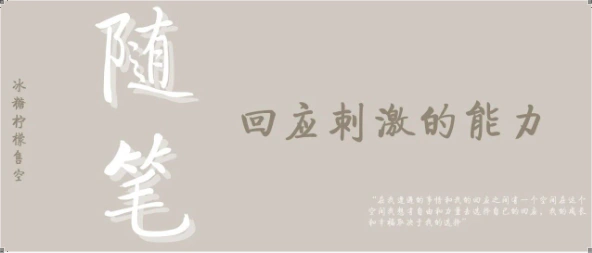
走上街戴上耳机听到一些歌曲,偶尔会灵光闪现,街道好似我灵感的容器,漫步带来轻柔的触感,而这首歌就如同热牛奶和甜蜂蜜,让文思温润地涌现。最近这首歌是《夏日漱石》。踩在雨路上,不止一次飞奔到家提起电脑包,又冲往咖啡馆,点好咖啡,把电脑撑开,文字却缩进了风衣口袋里,巧克力曲奇也哄不出来。它偏爱冷风,路过,街景。
刚进大学,会有瞬间异常悲哀,我度过了一个没有大事件的模板一样的人生,至少前十八年。说起来这也不叫生存啊,生存就是模仿一条安全之路吗?
我和根苗正红的中国无产阶级家庭养育的子女一样,学了十八年一堆现在早已经记不起来的应试学科,走上了一条没有家庭背景人大多数都会走上的路,进入大学,不出意外,会在家庭和社会压力下被迫读个研究生,再进入工作。
没劲。

所以我羡慕掌控自己人生的角儿,或者说,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干出事业的同龄人。我实在是见过太多了,各种官方公众号推选的精英分子,科研领域的翘楚天才,职场得志的仕途达人。
我处在一个,社会暴露推销精英的时代,大数据精准投喂尖端文化,我知道我离他们太远了,我一边感叹这些主儿真是牛逼冲天,一边放任自己在平庸中流亡。
不得不承认的是,我对于外界刺激逐渐变得病态宽容。我给自己安置借口,美其名曰这是因为我性格更加温和,安慰自己躺平就好。但是我清楚得很,麻木,固执,妥协渗入其中,混为底色。
我仔细剖析我的麻木,发现里面刻满了无力。但是每一条刻痕里,却又找不到“改变”的痕迹。我处在舒适圈里,拒绝刺激带给我的反思,我自怨自艾又可悲可笑。
早几年如果被嘲笑被挖苦被贬低,咬牙切齿大半夜,翻来覆去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下去心中的鬼火,将对方意淫成自己的终身大敌,抠破脑袋想着要如何去证明自己,让其屈服受降。
不知现在的我会称呼当时为幼稚。 还是当时的我笑话现在棱角磨平。
有段时间读书,看到史蒂夫·柯维讲到一篇故事,里面有句话:
“在我遭遇的事情和我的回应之间有一个空间,在这个空间我享有自由和力量去选择自己的回应,我的成长和幸福取决于我的选择。”

我像被打捞起来一样,拼命抓住这句话给我的感受:刺激和回应之中存在一个空间,我的能力,成长将被滞留于其中的被我把控的力量定义。
我想欢呼这其中的自由气息。
我想,或许我还可以尝试一些猛药,去尽情改变,而不是趴在失望失意旁,任由他们的手指顺过我后颈上的毛,给我喂着麻木咀嚼棒。
我他妈的才十九岁。该死的浪漫的十九岁。
我承认我进入大学患上急功近利这种顽疾,具体表现在看了一段公理定义就要把课后习题给干完,刚刚听完一首歌就要匆匆忙忙地打开琴箱稀烂地把它弹唱出来。在那段时间里,我失去了坚持和耐心的品质。
不过这句话带给我的奇妙魔力就在于,我变得不那么急躁了。

我知道我处于一个回应的阶段,这个阶段我调整自己尽量少受刺激带给我的负面影响,我自由地掌控着我的力量,我有力地挥舞着拳头砸向糟蹋我美好十九岁的破烂玩意儿。
于是我开始满怀期待着去尝试着新奇玩意儿,接受新的挑战,尽量少去想那些容易让我重新趴下的故事。遇到一些短期难以化解的尖锐问题,我不再去选择在几瓶啤酒里面寻找良夜的安稳睡眠,也不再挥霍我掌控的自由能力。
我开始静下心来阅读,学习,思考,反复练习,接受枯燥与孤独偶尔,当然,也会去适当防空。每每又有诱惑摆在我面前时,我可以选择沉沦自己于过往的遗憾中顾影自怜,也可以图一时愉悦拒绝延迟享受,但是我又会想起那句话,我的成长和幸福取决于我的选择。
或许突然从悲观到乐观主义有些许回光返照的意味,但是也回光返照这么久了,就当我康复健全了吧。
千万不要好奇我到底在干些什么,我正在这个空间里通过努力变好。
祝一切顺利。